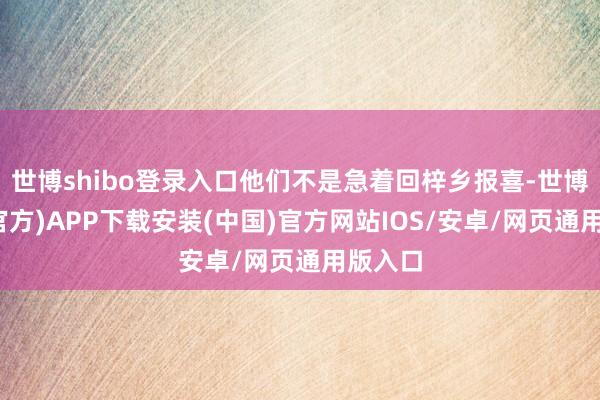
三千女子,跪在雪地,披着羊皮、裸着上身,被绳索牵着绕庙三匝。八十席贵客危坐不雅礼,金军亲王骑马围看。这不是处决,却比处决还绝对。
靖康元年,这场被称作“牵羊礼”的典礼,在金国太庙前演出。徽钦二帝在队列前头,皇后妃嫔在队列中间。礼走完,命没了。
有东谈主跳井,有东谈主咬舌,更多东谈主无声无名隐藏。她们为何不苟活?不是脆弱,是没退路。从那一刻起,命不是命,脸值过一切。
羊皮下面,不是皮,是一口闷头气靖康元年正月,汴京腐烂。金兵破门而入,抢完皇宫,还不浮躁走。他们不是急着回梓乡报喜,而是要好好安排一场“大典”。
徽钦二帝、皇后妃嫔、宗室公主、内宫命妇,全打包奉上北路,三千多名女子,一齐押送,队列宽敞。
走到金国上京太祖庙门口,等着她们的是一谈限定——牵羊礼。这可不是文雅礼节,而是羞耻典礼。
张开剩余81%过程明晰:女东谈主脱去外套,披上一张羊皮,草裙遮身,手反缚,脖子系绳,由金兵牵着走;男东谈主也跑不了,腰缠锁链,跪行三匝,磕头百次。周围高台设宴,摆了八十座玉案,金国亲王、高官、客东谈主骑马围不雅。
这方法,真称得上是:东谈主没死,脸先丢了。朱皇后就在这支队列里。她站在雪地里,被喝令脱衣,被动暴露胸口行“献乳礼”,就地承辱。本日晚上,跳井自杀。
过后还有更狠的。施礼完,被分给金国将领的称“赐女”;被关进“浣衣局”的,沦为军中杂役。命妇变侍女,贵妃变洗工。之前跪的是庙门,后头跪的是刀口。
这一场牵羊礼,不光是个东谈主羞耻,所有北宋王朝的脸被按在地上磨。她们披着的羊皮,遮不了冷,也挡不住孤苦泥。更挡不住接下来的东谈主间煎熬。
她们不是撑不住,是没东谈主给她们活路事情发展到这一步,为什么三千女子中,大宗接管了自杀?
其时期,女东谈主从小就学“清规戒律”:父命、夫命、子命。出了门,讲“贞节”;谢世,要“灵活”。这灵活两个字,重过天高。一朝失了节,哪怕没死,也算死了。
是以,这牵羊礼一走下来,不论是不是自觉、不论是不是被逼,只须体魄表露、被东谈主看见,就还是没了活路。不信看朱皇后。她成立腾贵,遭此奇辱,绝不迟疑跳井。
后头还有一长串名字,大意没名字,只被汗青写成“某氏”“宫东谈主”。她们不是不思活,是没法活。
她们的侥幸,写得干脆。被押北上途中,有东谈主投井,有东谈主投河,有东谈主撞柱。逃不出去的,就在夜里暗暗咬舌咽气。但写她们的东谈主,频频浮光掠影:“未归”“已卒读”,连名字都不配一个。
兼并场押送路上,有东谈主谢世转头。那是徽宗。宋徽宗被俘,在金国活了二十多年,如故写画赋词,喝酒谈诗,还和金国女子育有十四个孩子。汗青没说他辱没,反倒夸他情调优雅。
女东谈主施礼,是耻辱;男东谈主施礼,是忍辱。
北宋轨制下,女东谈主若是没了灵活,就连家门都回不去。被家东谈主接转头,不是团圆,是晦气。族谱不录,宗庙不供,一世无名。活下来,比死还痛心。
她们莫得接管,是社会提前替她们作念了接管:只须过了那谈典礼,就别思谢世转头。
东谈主站着,骨头是折的,脸还挂在树上押送队列临了走进了金国都城,地名叫五国城。
徽宗在这住下了,写诗、弹琴、养鸟,还娶了几个金国女子过日子。有东谈主说他“晚年闲隙”。而和他一谈来的三千女子,大部分隐藏在汗青的行间。
她们没死于刀剑,而是死在轨制和名节之间。她们的死,莫得碑文,莫得墓志。唯有汗青上一句“从者齐卒读”。
而活下来的,也不一定是谢世。被“赐浴”的命妇,被送入“浣衣局”的妃嫔,她们的日子莫得纪录,只留住一句“供役金军”。到底怎样“供”,没东谈主写。这类翰墨越简约,真相越千里重。
更特根由的是,金东谈主压根不护讳。他们在祭祖典礼上,明确晓示:“俘宋二帝二后,献礼太庙。”还专门编排“女子示辱”,称之为“胜国仪”。
若是哪位女子真能谢世转头,家眷也不会接。回家,是笑柄;不回,是千里默。于是,活东谈主成了活鬼。连名字都不见,身份也没了,仿佛历史里从来莫得她们。
靖康耻,说的是国度之辱;牵羊礼,说的是东谈主被当物羞耻。
不是说男东谈主不丢东谈主,而是男东谈主难看不致命;女东谈主难看,要命。三千女子,走在冰天雪地,穿戴羊皮,脖子拴绳,面向太祖庙的那一刻,还是就是判了生前死刑。
天子还谢世,王朝没了。东谈主还跪着,脸丢光了。所有北宋朝廷世博shibo登录入口,最终败在这场礼节上——颜面作念得太足,骨头早就散了。
发布于:广东省